与多半处于仆从状态的先人比起来,我们似乎幸运些:终于也有了自己的仆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公仆们形象光鲜,器宇轩昂,经常从电视屏幕上献给我们可掬的笑容。然而,他们终究是我们眼中的陌生人,我们注定没有近距离认识他们的任何机会。没有迹象表明,我们与公仆之间的距离会很快消失;由这种距离所维系的陌生,无论今天或今后,都为公仆们认可、欣赏与竭力维护。
亲民的神话
如果谁说我们的官儿不亲民,那真是没长眼睛!瞧,你看挂在墙上的这幅画有多感人!那么多张甜蜜蜜的笑脸将大人物围在中心,这还不是首长亲民的明证?
首长们还不只是在画像上亲民,亲民的机会可多着呢。
当然,亲民的第一证据还是首长的著作,那里面对老百姓的那份真诚、热情、关切入微,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受感动。这类著作中,“人民”二字出现频率之高,世上无出其右。
在人民面前的那份谦卑,西方政客是永远不能理解、更不能效仿的。至于直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那更让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羞死!
第二证据就是对老百姓的亲切接见。我就有幸亲历这种接见,那种让暖流电击般地穿透全身的幸福感,实在没法对你细说。
唯一的遗憾是,大人物离得太远了点,也站得太高了点,还在那个著名的城楼上呢,要不然,说不定早就和他说上话了。首长是那样慈祥、亲切、笑容可掬,要不是远了点,他是绝不会拒绝与老百姓攀谈的。不过,大手一挥的那个伟大镜头却很清晰,至今历历在目。
在城楼前被接见的那种幸运,毕竟难得时时降临。幸而有电视这一现代技术提供了替代的机会。现在,我们终于能够每天在电视机前与首长相见了。
首长离得那么近,简直就在眼前,由笑容所牵动的每一条皱纹都看得一清二楚,所讲的话语也听得句句真切。只差了一条:他没法听到你的声音,当然也不可能看到你;否则,那就真是天天被首长接见了。
虽然有这点遗憾,首长几乎每天从电视上注视着老百姓的那种亲民,还是足够感人肺腑;否则,人们每天准点看《新闻联播》的热情怎么会那样高呢?那些格外虔诚的男男女女,不正是在面对屏幕上那熟悉的面容时,对“大大”的神往呼之欲出吗?
电视上所显示的,远远不只是特写的面容,更有种种真实而热烈的亲民场面。
你瞧,那不是首长亲临工厂车间的画面吗?对众星捧月般围上来的工人们,首长嘘寒问暖,那种亲切,岂不世间少有,无怪乎工人们透出幸福的笑脸有如绽放的鲜花。
略感遗憾的是,工人与首长还是隔着点,其间还站着一大群随从官员或者安保;况且,也不是随便哪个工人都能进入现场,总不能丧失革命警惕性啊。
首长在兴致特高的时候,甚至会深入食堂与职工一起进餐。这种时候,亲民活动就达到了高潮,电视机前的观众,大概早已热泪盈眶了。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还远远不只这些。瞧!眼下就要随首长进入一户百姓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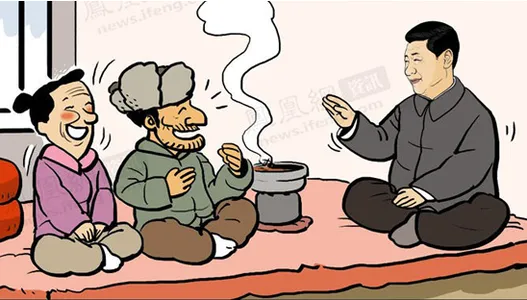
颤颤巍巍的大爷大娘坐在首长旁;首长仍然是那样慈祥、亲切,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不用说,这户人家的幸福感将存之永远,传给子孙后代。
中国老百姓不下十亿,能在家中接待大人物,其机会之稀罕,也算中头彩了。我不免有点好奇:那户幸运人家是怎么被选上的呢?肯定不会是依据抽签。
记得在一篇报刊文章中看到,1980年代,胡耀邦在巡视地方时,突然有意改变预定路线,将车拐入一户农家。这一临时决定的家庭访问,让随行人员慌了手脚。由此可见,大人物随机访问百姓家这种事情,不过偶尔有之。因此,这种给人幸福感极高的亲民,必定是高度选择性的,其宣传价值远远高于实质意义。
从电视屏幕上透射出来的亲民,总体上该如何评价呢?
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首长形象,确实尽显谦逊、亲和的风度,与刻意讨好选民的民主社会领袖似乎并无二致,甚至过之无不及。
不过,没有人抱有奢望,能在电视屏幕之外的现场,实际接触高山仰止的首长们,这种事情依然存在于传说里。
将大人物与升斗小民隔开的那段距离,仍然十分遥远,在短时间内,没有任何希望能显著縮短。
首长与老百姓的关系,理论上当然是亲密和谐的,但那种隔膜与疏离,却真实存在,实际上已写在老百姓的脸上:在官儿们面前,哪个老百姓没有一张惊恐不安的脸!正是这一张张惊恐不安的脸,大大抵消了电视形象所创造的亲民效果。
在逐渐明白起来的人看来,在多年中被刻意包装的亲民,越来越像一种遥远的神话。今天,或许上上下下都心安理得地满足于这一神话。
熟悉的陌生人
通过电视,我们熟悉了那一张张可亲的面孔,其中包括每一代“核心”,也包括各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所有“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能轻而易举地认识这样多的大人物,实在是这个电视时代的光辉,更是当代人的幸运。
然而,我们心中十分清楚,对大人物们的熟悉是很有限的,非常空洞,甚至显得虚假。我们不可能真正熟识他们,毋宁说我们根本不够格,不配享有这种幸运!
你大概听说过薄一波,就是那个著名的重庆王薄熙来的老父,他在革命元勋的“万神殿”中,至多算一个三流人物。他能真正亲民、或者有亲民的意愿吗?
在开始文革的那个乱哄哄的1966年夏天,高干的架子已经大不如前了。当文革闻人蒯大富在校园内偶遇薄一波,问他一些问题时,薄一波直接告诉蒯:你没资格和我说这些!
应当说,这不是傲慢,而是坦言;即使是最低调的中国官员,其内心也不能不这样想。高官与小民之间的距离,就是有那样遥远,并不是一点点谦逊可以克服的。
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十多亿人的大国啊,大人物们日理万机,哪能经常接近老百姓或被老百姓挨近!说得一点不错,没有人反对;况且,无论大国小国,全世界莫不如此。

这似乎注定了,任何国家的要人与民众都是疏离的。但“此疏离”与“彼疏离”,并不完全一样,至少有两点区别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是,我们的首长能够根据形势的需要与自己的意愿,选择性地亲近某个老百姓;但任何老百姓却无权随机地“幸遇”某位首长。
与此相反,在民主制度下,政界要人不太可能断然拒绝某个随机地接近他的选民。
这意味着,介于东方领袖与其民众之间的那堵墙,任何小民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力量突破;在西方领袖与民众之间,当然也少不了有一堵墙,但它挡不住任何坚持以合法方式进入墙内的人。
其二是,两者奉行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东方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决定了,领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斯大林语),是“大救星”,甚至是“红太阳”;他在任期内绝不容许任何最轻微的批评;他身兼政治领袖与精神导师,是不容怀疑的最有智慧的人——总之,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谁敢和他套近乎?
西方价值观没有给政界领袖任何特殊地位,领袖与任何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平等可不是做样子的。一个公然在大街上痛骂奥巴马的人,根本不必担心会因此而入狱。在地铁车厢内站着的卡梅伦(在其首相任内),别指望有人会给他让坐。
这样的照片风传全世界,根本不是用来说明英国政治出了什么问题,仅仅是为了表现一下因政务不顺而失魂落魄的卡梅伦而已。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政界要人与民众的隔膜都是不可避免的。就此而言,说我们的领袖高高在上,也算不了特别不敬,因为普天之下莫不如此。区别在于,我们这里的隔膜是制度性的,是制度设计特别允许甚至刻意造成的,任何胆敢冲破这种隔膜的举动,都将面临严峻的法律后果。
而在西方,上下层的隔膜主要导因于客观情势,源于沟通不畅的现实原因,它不是法律允许下的坚不可摧的墙。
这一切的后果是,在我们这里,经常出现于电视屏幕上的那些大人物,无论其面孔如何熟悉,他们终究是我们的陌生人。
陌生的广度与深度都非同寻常,致使他们与常人之间的距离更加无法跨越。
首先,你永远不知道首长们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政要们都谨言慎行,在公开场合,从不多说一句话;即使登台讲话,也多半照念秘书准备好的稿子,让别人去猜测讲话后面的潜台词。
老百姓总习惯于认为,坏事都是下面人干的,而大人物则总是维护着老百姓。大人物的个人信息,例如他们的婚姻状况、家庭情况、健康状况、个人爱好,似乎都是国家秘密,宁可让小道消息流传,也不让正常信息渠道畅通。
至于高层的日常生活、相互往来、思想交锋、决策过程、权力博弈,更加是头号国家机密,老百姓根本无从得知。
凡此种种,都使要人们犹如深居天宫的上界真人,真正超凡脱俗,完全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与想象,留下的唯有隐蔽与神秘。这样,在老百姓眼中大人物们岂能不陌生?
陌生有什么不好呢?对于要人来说,“陌生”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保护。举凡一切不宜让老百姓知道的东西,诸如秽德、暴戾、低能、猥琐等等,或许皆因陌生而不为外界了解。更大的好处是,正是陌生造成神秘感,而这正是威仪与力量的源泉。在常人看来,这种道理或许匪夷所思;但在要人们看来,这简直是新手也懂的庙堂要诀。
威仪的代价
一些本来来自民间、一开始未必会摆谱的人,怎么到了有资格上电视的时候,就会官气十足,最终成为民众眼中的陌生人呢?这涉及权力的起源,或许还不是一个很肤浅的问题。
树立官威也是需要学习的,并没有什么人天生就能够且乐意演大人物。很不容易进入角色的人物,古今都不乏有趣的例子。
刘邦以一个乡下游民,在群雄竞逐的秦末乱世,终于取了天下,没有人否认他是一个盖世英雄。但一个乡下人,哪里懂得应如何做皇帝?
在很长时间内,刘邦都改不了他的粗野本色,甚至不介意往儒生的帽子里当众撒尿。这样的形象,岂能在与他一起打天下的群臣面前树立威仪?
但一旦听信了儒者叔孙通的进言,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朝仪,朝堂上冠盖如云,山呼万岁,皇帝的威仪就立即显现,再没有哪个昔日小兄弟敢与他称兄道弟了。
彭德怀只是一个武将,并无觊觎大位之心。他与刘邦一样,也是一个粗人,而且终生都未进入角色,平生厌弃任何官场做派。他身为国防部长,访问东欧时竟不顾礼仪,喝令欢迎他的仪仗队解散。只是他后来惨遭整肃,这些毛病就无关紧要了。
抛开这些事例不说,仅仅依常理而论,任何依靠官僚系统进行管治的国家,大人物没有一定的威仪、没有不失神秘性的形象、与部属及民众没有一定的距离,恐怕是不成的。如果适度地认可这番道理,对于那些“电视上的陌生人”,就多少应给予一份理解。
问题在于,公仆们也许走得太远了,已经不仅仅是陌生而已,与民众之间的隔膜已成了巨大的鸿沟。威仪或许有了,但其代价却十分沉重。
在这件事情上,不妨撇开价值观,我们的文明还远没有那样精细;基于功利主义的观察,是一个更好的视角。直白地说就是:从公仆们的利益着眼,过度地追求威仪是不值得的。

首先,上下之间的巨大疏离,势必完全遮挡权力者的视线,让真实的社会图景,不再进入权力者的视野之内。这就不免严重误判社会的情势和舆情,进而影响到决策的有效形成与实施。这对于执政者来说有什么风险,历史已提供够多的启示。
再者,如果成天在电视屏幕上风光无限的人,并不具有人们所期待的那种亲和力,而是民众眼中的陌生人,你将用什么去激发下属与老百姓的热情呢?在当今这个充满挑战、险象环生的世界上,普遍的冷淡绝对非执政者之福,当然更非国家之福。
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在我们这个金字塔结构的社会中,高层的任何形象设计,都会立即成为各级官员的榜样。
我曾亲历的一件事可不是传奇。就在北京大检阅之后不久,一个地方小学院有样学样,也搞了一次像模像样的检阅,当领导坐着敞篷车,在学生队伍前高呼“同学们好”时,下面竟然“首长好”的呼声雷动。试想,如果大人物成了电视上的陌生人,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那些有样学样的小官员会同样成为老百姓眼中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