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威尔能不当护国公吗?罗伯斯庇尔能不使用断头台吗?洪秀全能不大开杀戒吗?慈禧能不垂帘听政吗……。没有人敢说,这些行为绝对不能阻止,但肯定不那么容易。那么,这些不得不行的选择究竟关乎道义,还是关乎时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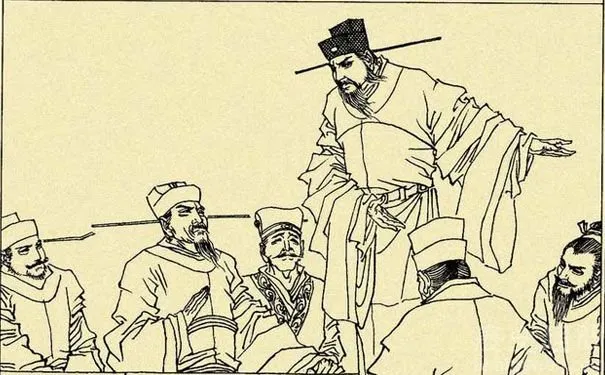
王安石变法
近代谈变法者不可能不提到王安石。确实,王安石变法声播古今,它历时之长、涉及面之广、争论之激烈、过程之曲折反复,都是史上仅有的。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因而王安石也就成了历代改革者的一个悲剧性标杆。
王安石(1021—1086),临川(在今江西)人,21岁中进士,历任多处地方官,政绩卓著。1058年,王安石上书提议变法,但未被宋仁宗采纳。神宗即位后,开始重用王安石。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在神宗的支持下全面推行新法。
王安石的新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均税法、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等,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变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改变北宋多年积贫积弱的局面;其重点自然在财政经济方面。用现代语言说来,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试图运用国家力量,全面管制社会、经济生活,并在官府主导下运用某些经济、金融杠杆,促进社会经济活动,增加财政收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其中一些变法,如青苗法、市易法等已包含现代经济、金融思想的某些元素,其推行之难可想而知。
变法引起了激烈党争,新法亦迭经兴废,伴随着王安石的几度沉浮。随着变法引起的矛盾与困难日益增大,变法的势头渐趋低落,到神宗去世时(1085),主要的变法活动也就终止。后来虽几度恢复,其余波延续至北宋末年,但一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某些方面甚至造成了真正的社会灾难。
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现代论者多强调贵族豪门的反对、变法急功近利、政策执行不力、用人不当、改革派内部分裂等等。这些都是表层的原因,不足以解释一个由皇帝主导、历经数代的大规模运动,何以完全不能生效。本质的原因只能是:在一个社会、经济处于低组织水平的时代,试图以国家力量全面管制社会、经济生活,是一种过于超前的空想,在当时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变法“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都不曾在当时世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不容其他类似因素分庭抗礼”。
在今天看来,令人奇怪的倒不在于变法的失败,而在于变法者屡败屡变,即使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宋神宗与王安石都谢世之后,变法依然几度复起。这并不能用变法者的毅力与坚持来解释。真正的原因在于情势而非人事,情势并非人事所易改变。
就情势而言,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某些变法措施具有不可逆性,不是哪个人能够说变就变、说停就停。例如均税法完全改变了田赋征收的格局,即使旧派官员当政,哪能轻易推翻新法?其二是对于新法形成了某种依赖性。变法的一个最显著效果是,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因此而相应地增加的财政开支,不可能因新法废止而立即取消,这就使得存在复行新法的动力。
由此可见,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官员,面对变法造成的既定局面,对于新法存废都面临一种欲罢不能之势,并不容易靠官员的个人倾向与意志改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形势比人强。人们容易指责王安石及其后继者:明明看到新法造成了严重后果,却不肯立即收场,改弦易辙,岂不是有意祸国殃民?其实,当局者所面临的情势与难处,局外人是很难理解的。
慈禧归政
慈禧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无论其得失如何,都是被人们深深厌弃的。内宫干政,历来遭人非议,更何况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由后宫主政半个世纪!
慈禧(1835—1908)原不过是咸丰皇帝的一个“贵人”,只因她为咸丰生了一个儿子,就在后宫确立了其优势地位。1861年咸丰离世,慈禧的儿子继位,是为同治皇帝。慈禧与慈安并尊为太后,共同“垂帘听政”,实际上慈禧几乎独揽大权。此后近50年中,慈禧事实上就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以致在某些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就是“女王”当政,似乎慈禧就如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坐在王位上。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她干的几件大事岂止不让须眉,简直是惊天动地。她刚刚执掌权柄,立即就联合小叔子恭亲王发动政变,诛杀了咸丰留下的顾命大臣,完全控制了政权。1875年,年仅19的同治病故,慈禧又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其妹妹的儿子继位,是为光绪;慈禧仍然执掌大权。1884年,慈禧策划罢免恭亲王,此后实际上完全独掌朝政。1898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废止维新。1900年主导了借义和团对抗列强的运动,导致庚子之变,酿成八国联军入京的惨祸。
当然,慈禧的50年统治也并非仅仅玩玩宫廷阴谋而已。这50年恰逢中国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不断,情势变化万端,重大决策实际上都要经过慈禧之手,无论成败得失如何,那副担子岂常人所能担当?慈禧一女流之辈,生活于后宫,对于外界不可能有太多知识。几十年执政生涯,断事无数,其智力绝非等闲。况且,其治绩也并非一无是处,她执政的前15年可谓太平安定,甚至被誉为“同治中兴”。
慈禧的厄运在于,她当政的年代,恰好是中国在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下,国势日益衰落的年代,也是受西方影响的新兴力量对满清的挑战日益强势的年代。时代潮流之强大,岂止慈禧抵挡不了,就是康乾再世,也只有徒叹奈何。但无论当世人还是后世人,都未必能深悟这种时势的力量,只是专注于从当道中挑选罪人。这样,慈禧就只有充当国家失败的祸首了。她也罪有应得,谁叫她赖在位子上不下来呢?
看来,慈禧完全可能有不同的选择,选择的机会就出现在1861年、1875年、1884年、1889年、1898年……,每一次她都可以选择放弃权力。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始终紧握权力,直至咽气之时。她这种执迷不悟的恋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正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权力无疑对任何人都有巨大的诱惑,对慈禧这样贪权的女强人尤其如此。慈禧是否一直迷恋着权力,即使年老力衰之时仍不想放手,今人已不可确知;或者这一点已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慈禧敢放弃权力吗?
1861年,慈禧能不要权力吗?即使她读书不多,未必知悉刘邦的薄夫人的故事,她不可能不知道咄咄逼人的肃顺等八顾命大臣的威胁。当时只5岁的同治保护不了她,同治自己的命运都握在别人手中;她也不能完全信任小六子。这样,她就只能每日坐在帘子后面监管着权力了。
1875年,慈禧敢放弃权力吗?亲生儿子都不在了,光绪固然是亲侄子,但毕竟隔了一层;朝中王公大臣虎视眈眈,有哪一个可以完全信任?她那时不过40岁,谈不上根基完全稳固,还是亲手握权才放心啊。
波诡云谲的1898年,慈禧就更不敢放弃权力了。光绪本来是一个懦弱的孩子,自幼在慈禧的监护之下,似乎不敢有什么违拗之举。但世事难料啊,多年的欧风美雨,也让这个长于深宫中的君主心生邪念,居然玩起什么维新来了。维新且不说,任用新党,排斥旧臣,新政全出于康梁,心中竟全无一手提携他的皇阿妈,这样下去,岂不将使她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凡此种种,都使慈禧不敢甩手归政;就是有几次真正归政的好时机,最终还是放不下心,交权的手伸出去又縮了回来,欲罢不能啊!
汪氏降日
汪精卫这个大汉奸,无疑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但粗通历史的人都知道,就是这同一个汪精卫,曾经是“从容作楚囚”、行刺满清摄政王的勇士;是国民革命时期的左派;是孙中山遗嘱的实际起草人;是1930年代初期抗日的积极鼓吹者。一个有如许辉煌经历的人,在日本卵翼下的南京伪政府内,他会如何思考自己的过去未来呢?
汪精卫(1883—1944),出生于广东三水。他早年是孙中山的亲密追随者;袁世凯统治时期留学法国;回国后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1921年任广东省教育会长,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5年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山舰事件后出走法国;1927年归国后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随后又出走法国;回国后于1932年任行政院长,位置仅在蒋介石之下。
918事变后,汪精卫摄于日本威势,认定抵抗无望,渐渐滋长求和心态。1938年之后,日益醉心于主和。早与日方暗通款曲的周佛海,极力说服汪精卫向日本求和。1938年底,汪精卫终于离重庆出走;1939年建立南京伪政府,此后成为日本人的工具。
汪精卫无疑是极富才具之人,且早年经历亦不乏光彩,因此曾有众多仰慕者,在国民党内一度是蒋介石的有力竞争者,汪蒋两人的瑜亮情结甚深。汪氏晚年大节已亏,其历史定位不复可言。但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历史人物,汪氏晚年的心路历程,仍然是人们的关注兴趣之所在。
汪精卫少时失怙,过着“以长兄为父”的生活,养成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性格。早年革命活动中,虽然可以说少年得志,深得孙中山赏识,但关键时刻常常举棋不定,反复无常。汪妻陈璧君来自南洋富商之家,慕名追随汪精卫,美誉播于海内外,但对汪的钳制亦影响至巨。不少论者认为,与蒋介石争领袖之位而不得志,是汪氏出走的重要原因。以汪氏一生行状来看,其权欲似不至此。但陈璧君与汪精卫左右都不乐见汪屈居蒋下,则是事实。在关键的1938年,正是陈璧君与周佛海等人,给予了汪精卫最大影响。这些因素,对于解释汪精卫的行为逻辑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欲罢不能
为情势所迫欲罢不能,这种体验人或有之,并非仅知名人物而已。这就可提出有点普遍的问题:倘“不能罢”,将有何结局?最终是喜还是悲?“不能罢”的原因是什么?
依结局是喜是悲,可区分出两种情况。
如果是喜的结局,那么你就走在一条上升的道路上,前途似锦啊,那个“作罢”之“欲”,从何而来?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谈不上“欲罢不能”。如果你实在有“欲罢”的意向,必定处在某种很特殊的情势之下。例如,下述情况都可能使你知难而退,作放弃之想:力不从心,即便成功在望,也觉得劳累难耐;最后结果固然诱人,但风险巨大,难以承受可能要付出的牺牲;虽然期望摘冠,但在强大的竞争者面前,没有信心,如此等等。
既然“欲罢”,为何又不能呢?一些可能的原因是:
1) 高速上冲的惯性巨大,无法遽尔止步。
2) 已与他人形成某些利益攸关的联系,不可能单独止步。
3) 发现一旦止步将面临重大风险,除了继续前行别无选择。
现在来分析一下王安石变法这件事。既然对它大体取正面评价,自然将其成功的结局视为好事。王安石阵营中的某个官员,可能因为畏难,可能因为害怕风险,也可能因为不想卷入与同僚的竞争,萌生退意,也就是“欲罢”。但是,因为他已深度卷入,或者因为他被同党裹挟,或者因为他意识到中途退出可能获罪,他已经不能退出,只能铤而走险了。而这就是变法者的欲罢不能。
如果是悲的结局,这意味着你在一条下行路上行将滑向深渊,“欲罢”是很自然的,除非你愚不可及,竟毫无知觉。尽管你急于刹车,脱离险境,但未必能如愿,如下的理由都可能让你“欲罢不能”:
1) 高速下滑的巨大惯性,让你无法止步。
2) 被命运相连的同伴裹挟,不能单独退出。
3) 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控制,试图脱身但恐遭不测。
现在来分析一下汪氏降日这件事。当年的孙中山战友、革命义士堕落为汉奸,当然罪无可赦。至于汪氏在降敌过程中,是否有过“欲罢”之念,只有史家去考证了。能肯定的只是,大错铸成之后,他即便萌生退意,恐怕也为时已晚。1938年他出走河内时能金盆洗手吗?已大量公开的降敌言论如何洗脱?1939年时他能改弦易辙吗?一生惧内的汪氏首先就过不了陈璧君这一关,也绕不过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裹挟。1940年之后他能毅然回头吗?他岂不知残暴的日本人绝不会放过他?这样,除了将汉奸角色演到底之外,他再无选择余地了。汪氏生命的最后两年,极为消沉,岂不是其内心为“欲罢不能”所深深折磨之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