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华两千年来都是泱泱大国,人文昌盛,礼仪之邦。虽然四夷臣服,万国来朝,但真正追随华夏文化的学生,却数不出几个来。就连贴身近邻蒙古、老挝、缅甸诸国,都未进入汉文化圈,汉字都不曾识得,更不说接受精妙深奥的孔孟之道了。
出人意外的是,一个并非贴身近邻的海外岛国,倒成了汉文化的热心追随者,而且几乎一直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它不仅使用汉字,是汉文化圈中除中国外迄今文字尚未拼音化的唯一国家,而且擅长汉文的诗词歌赋,几乎全盘接受了包括儒学在内的汉学,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与老师一较高下。这个优等生就是日本。
由于日本孤悬海外,与中国没有边界纠葛,从开始官方交往的隋唐时代起,直至晚清的1500年中,彼此相安无事,只是元初及明代有过短时间的兵戎相见。正因为如此,后来友好接触时中日高官才能大谈“自古以来的友好邻邦”。
但到19世纪末,形势陡然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睦邻兼学生竟然成了宿敌。并非中国有什么事情开罪于日本,而是日本拜了西方这位本事更大的老师,迅速成为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列强,不再看得起过去的老师,而且想侵夺老师的利益了。这样一来,近一个半世纪中,两国冲突不断。往好里说,这叫做一对师生间的百年竞争;往坏里说,那就是东亚势不两立的两雄之间的生死斗了。不管是和平竞争,还是生死搏斗,反正免不了一场斗智、斗勇、斗力的跨世纪博弈,互为宿敌,至少也是对手。传统上我们从来都不很看得起对手,数落起“小日本”来尤其快意。只有深思之士才会认真去想:中日之间的历史性竞争,胜负记录究竟如何?今日之博弈,我们是否稳操胜券?这可是事关民族尊严与国家安危的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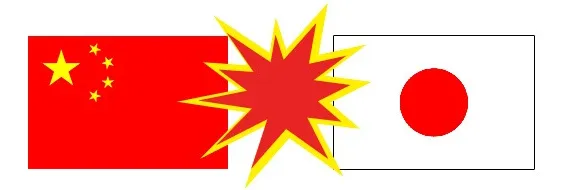
For two thousand years, China has been a great country, a prosperous human culture and a state of etiquette. However, very few nations in the word has been influenced by China, Even the close neighbors of Mongolia, Laos, and the Burmese countries have not entered the Han culture circl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never been known, let alone accept the subtle and profound approach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Surprisingly, an overseas island nation that is not close to its neighbors has become an enthusiastic follower of the Han culture and has almost always been the best student in China. Not only does it use Chinese characters, it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that has not been pinyinized so far except in China. It is also adept at poetry and poetr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as almost completely accepted Sinology, including Confucianism, and in some respects even with teachers. Higher down. This top student is Japan.
As Japan hangs over and hangs over the borders, it has no disputes with China. From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at began official exchanges to the 1,500 yea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was nothing wrong with each other. It was only in the early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at there was a brief battle between soldiers.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is that when senior officials from China and Japan later talked about friendship, they would be able to talk about "friendly neighbors since ancient times."
Japan has been a only very good student of China in the in ancient times, However,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situation had suddenly changed, and the original good-natured student and student became even a favorite enemy. It is not that there is anything in China that is committed to Japan. It is that Japan has worshipped the western teacher, who is the bigger teacher, and quickly became an equalizer with the West. He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be a teacher of the past and wants to invade the teacher's interests. As a result, in the past one and a half centuries,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ontinued. To say good things, this is called a century-long competi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the bad, it is the fight between the two males in East Asia. Whether it is peaceful competition or fighting between life and death, in any case, a cross-century game of wits, fighting, and fighting will become indispensable to each other, at least to rivals. Traditionally, we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look at our opponents. It is particularly pleasing to see the number of "Little Japan" falls. Only those who think deeply can seriously think about the histor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hat is the record of victory and defeat? In today's game, do we manage to win the game? This is a major issue that concerns national dign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维新之局
1840—1842年,中国历史性地败于一个从未较量过的对手:“蕞尔岛夷”英吉利。从噩梦中惊醒过来的林则徐,开始认真地检讨战争的得失,试图了解一直被忽略的西方世界,广泛地收集有关西方的资料,编了一部常识性的读本《四洲志》,相当于一部普及本的世界地理。林则徐进而嘱托好友魏源,要后者编写一部更详尽介绍西方的书籍,以作强国之资。魏源果然不负所望,于1847年发表了他的不朽著作《海国图志》,其中全面地介绍了主要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情况。
拿破仑曾称中国为“睡狮”,不少人竟因此而沾沾自喜,根本不在意这头狮子是否睡得太沉,竟误了那班高速前进的世界快车;尽管1840年挨了闷棍,却依然在昏睡不醒中白白耽误了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20年,无所知觉地等着下一次挨揍。像《海国图志》这样振聋发聩的醒世之作,竟然无人问津。
当时,小日本还没有被称为“睡狮”的资格——岂有人认为它也算得了狮子?虽非狮子,却也在闭关锁国中沉睡多时。但1854年佩里率领的美国舰队来临,终于惊醒了它的酣睡,知道世道已经变了。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日本人得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没有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弃若敝屣,而是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吸取了其中的海外信息。就是这本书,竟然改变了日本的命运,同时也使中国被动地交上了厄运,成为强大后的日本的第一个欺凌对象。实现日本命运转折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对于促成明治维新,《海国图志》一书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或许不容易确定;但明治时代的许多维新志士,读过《海国图志》是没问题的。这样一来,中国人仍然可以自豪:实现了维新的小日本还不是受惠于它从前的老师!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如何迅速崛起为一个东方强国,早已见于历史,不必细说;况且这也是一个听起来使人不快的故事。被自己从不以为意的学生超过,谁又能心安理得呢?
使后世人纳闷的只是,为什么日本人能维新,而中国人就不能维新呢?理由甚多,难以尽述。并非最不重要的一条理由或许是:中国从来都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岂肯折腰学习外夷番邦?日本却没有这种盲目自大心态,它几千年来一直都在学习外国人呢。
这样一来,在维新这一场竞赛中,中国就输了一局。幸好,中国并无任何失落感,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感到需要什么维新。
甲午之局
明治维新之后30年,日本与中国完全易位了:过去的学生已经成了老师。日本学习西方之快,崛起之猛,在世界史上也算是一个奇迹。此30年中,老大的中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长进,但那种日本式的维新,却还没有开始,且依然没有多少人认为有此必要。天朝唯一的进步,是意识到需要有坚船利炮。在花了无数银子之后,也算面貌一新了。最突出的成就,是由李鸿章主导建立了北洋海军,它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军舰,被誉为亚洲第一强海军。有了这个本钱,当时朝野没有人将小日本当回事。
也是冤家路窄,中日两国的海军偏偏在甲午年(1894)干上了。事情的根本原因,应当是日本对中国早有所图。鉴于它对中国老迈颟顸的了解,它似乎胸有成竹、底气十足。事情的直接原因是:两国掌控朝鲜的竞争,最终演变为军事对抗,战争在海陆两路同时展开。那些自恃有亚洲最强海军的文臣不断鼓噪,岂知先进军舰还得先进的人事主导?而没有经过任何制度改革的中国,恰好缺少这个。与之相反,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岂止海军现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观念都已相当现代化了,这种综合国力,哪是老迈腐朽的天朝所能抗衡的?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不过,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恐怕也超出了日本人的预想。
于是,中国又输一局。与上一场败局不同,这一局真正见血了,中国朝野不可能再无动于衷,终于跌跌撞撞地走上了变法图强之路。
二战之局
甲午之后,中日强弱之悬殊,即使再盲目自大的人,也有些明白了。此后的几十年,无论北京如何频繁易主,都没有人敢起而公开对抗日本人。中国方面自然吃亏无数,这些只能暂时记在账上;雪耻之日,则付诸未定之天。
但中国的忍让并未抑制住日本人的胃口。这个小日本竟然自不量力,居然想一口吞下一个庞然大国。于是,一场旷世未有的生死较量就在东亚大地展开了。此时的中国,固然仍然虚弱不堪,但人心之奋起,则远非甲午年间可比。纵然中华大地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抵挡寇仇的决心,却有增无减;日本人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终成泡影。也是天灭日本,这个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狂徒,不满足于鲸吞大陆,竟然挑起太平洋战争,致使二战盟国卷入其中,岂不找死!这样,日本人就只有陷入灭顶之灾了,最后还挨了两颗原子弹,做了一回核战争的试验品。
这一回,中国终于胜了日本,总算扳回一局。
但这一胜局却并非完美无缺。我们自己就不理直气壮,既宽恕冈村宁次等战犯,又放弃赔款,更不向日本本土派遣占领军;对手也不认输,至今欠中国一个诚心道歉。究其原因,固然有国共内战这一干扰因素,但最主要的是,日本人根本就不认为败于中国,只认败于美苏而已。日本的民族性数千年一以贯之:只服强者,不服公理!只要你不能将他打翻在地,让他磕头求饶,他就永远不会服输。二战过去已70年了,全世界都看得明白:日本对于美俄两强,哪敢说个不字?美国人成了他的大老板,这且不说;俄国人与他并非一家,谈不上亲密,还占着他的北方四岛,动不动要派战机绕日本而过,日本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哪里还谈得上跳出来挥拳弄棒?偏偏就对中国人屡屡无礼,岂不让几亿中华健儿怒火中烧,直呼“手下败将岂有此理”!
中国愤青们怒吼得有理!只是怒吼之余,务必悟出一个道理:
要让日本人服输,必得真正凭自己力量彻底地胜它一局!
复兴之局
战后中日两国都破败不堪,惨不忍睹。中国且不说内战期间继续烽火连天、血肉横飞,就是在建政之后,也是满目苍凉,百废待举。日本在战后则自食苦果,几乎一片焦土,频于绝境。两国同时面临战后重建,各自致力于复兴大业,不经意间成了一场赛局。这一局中国似乎能赢,而且也无颜再输了。
让全世界都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竟又输了一局!
我们本来已赢得了天赐良机,我们本来应当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举国一致,共建家园;我们本来要记取数十年内乱的教训,实现国内和平,杜绝内耗;我们本来要汇集天下英才,同赴建国大业;我们本来要让“耕者有其田”,“商者有其产”,业者获得最大的发展机会;我们本来要吸取人类一切知识,弘扬科学,振兴教育,让莘莘学子个个成为现代人才……。
然而,有人却认为这些全都是平庸之见,中国需要的是改天换地、阶级斗争,一年一场批判,两年一次运动,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反修、四清,直至文革的“全面内战”,让全世界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到1976年,总算演完了这幕大戏,经济已频于崩溃,哪里还谈得上复兴大业!
再看对手日本,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1946年,麦克阿瑟主导了日本的民主改革,天皇退居虚位,国家实行宪政,废止财阀控制产业,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军国主义的上层构架被釜底抽薪。经济一旦不再被绑架于军阀的战车,自由创业很快就成为风尚,其效果立竿见影,短短十年即实现了全面的产业复兴,从1960年代开始了经济的高速成长。到1970年代,恰逢中国深陷文革灾难之时,日本正式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经济进而实现全面起飞。
一败一成,何等惨烈的对照!在和平竞赛中败于宿敌之手,蒙受如此奇耻大辱,何颜面对当年国难中的先烈?
现代化之局
1977年邓小平复出之后,访问的国家不算太多,但他没有漏掉日本。他当然不会忘记率领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与日军周旋的艰难岁月;也不会忘记在文革劫难中眼巴巴地望着日本人遥遥领先,无可奈何。对于他,与日本联系在一起的想必是仇恨与屈辱。但现在他肩负着振兴国家的使命,而为此不得不去向对手学习。当他乘坐的高速列车行驶在日本新干线上时,他的感慨集中到一句话:
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
那么,今天的人完全明白了邓公这句话的含义吗?邓公未加解释的东西或许永远只能猜测了。在江西拖拉机厂前的那条小路上,就中国的过去未来思考过千百遍的邓小平,所希望的现代化,当然不限于高铁而已。在日本的高铁上,他能不想到日本现代化的由来,能不想到日本毫无保留的对外开放,能不想到日本全面学习西方的成功?邓公从日本回来,并未立即着手在中国修建高铁,而是立即推动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件事情千头万绪,今天人们已不容易详细回顾了。但其要旨实际上并不复杂,它不过是强调一个常识:
别人用以达到成功的方法,我们何妨拿来一试!
正是这一试,迎来了后来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我们无法知道,当年邓公在日本高铁上所想到的一切,今天是否已全部成为现实。能够肯定的是,今天所实现的一切,无论人们是褒是贬,是先邓而去的那位大人物完全设想不到的。
那么,在中国迅速奔向现代化的时候,日本人在干什么呢?他们当然不会闲着。不过,他们已经背负一个巨大的基数,有点步履蹒跚了,在快步前进的人看来,更近于在爬行。尤其是最近十年,全世界以及他们自己,都在谈论日本的停滞。就经济总量而言,日本的第二把交椅早已让给中国了。当然,日本人仍然有他们自己的自负:让全世界用户追慕不已的优质产品;享有盛誉的一流技术;高度安定和谐的社会;被全世界旅游者一致赞誉的公民道德与优美环境……。
那么,在发展更快、块头也更大的中国面前,日本究竟是傲然自得,还是自叹不如?它还敢轻视它过去的老师、后来的仇敌、今天的对手吗?或者,更干脆的问题是:在最近这几十年的博弈中,中日两国究竟是谁拔得了头筹?
如果依然没有肯定的答案,那么,这一场生死博弈就只有继续进行下去了。